博文
二启:清明泪雨——写在母亲诞辰百年的日子
||
在母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哥哥鼓励我写一篇祭文。他过去写过一些,往往是我的提醒,告诉他父母的忌日临近。我觉得他有写作的习惯,对我来说却比较陌生。但哥哥说我有写作潜力,只是被自己忽视而已。于是,我忐忑地提起了笔。
母亲生于一九二五年农历三月十三,恰好是当年的清明节。她们那个时代的人,生于烽火,长于离乱,虽然经历了家国的不幸,但战火淬炼了她们的坚韧,苦难铸就了她们的意志。
母亲出生在湖北广水杨寨附近的徐家亚元,虽然祖上发了点小财,买了田,但依然是个地道的农民家庭。母亲小时候很羡慕两个哥哥可以上学,她与外祖母抗争过多次都未能如愿。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国共两党在这个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达成共识,于1938年3月10日在各界知名人士、国际友人的见证下,在汉口成立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后陆续成立12个分会,45个保育院及三个境外保育院。
这是母亲走出去看世界的契机。1938年9月,一个大字不识的她和二哥及一些同伴,加入了这史无前例的“战时儿童保育院”。他们到达汉口再出发,辗转于湖南、广东、广西、贵州,路途常遭日军飞机轰炸,时有保育员为掩护儿童而不幸牺牲。我的二舅(母亲的二哥)也在途中病亡,母亲侥幸到达贵州后,被分配在第一战时儿童保育院,即青岩保育院,后改为贵州女子保育院。
保育院里除了学习文化课程,10岁以上的儿童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力求生活自保。母亲他们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边学习边劳动,自强不息,获得扎实文化基础。抗战胜利后,母亲顺利考上安顺军医学校学习护理,1948年毕业于上海。感谢哥哥,他正在安排我们兄妹三家人一起,在即将到来的6月,去青岩古镇和安顺军医学校旧址走一走,体验母亲在贵州的“抗战8年”。
随着新旧社会的交替,母亲于1951年进入应山县人民医院工作,重新开启了她31年的职业生涯。1954年10月1日,母亲和语文教师的父亲在县中学与三个同事一起举行了一场隆重的集体婚礼。那时候的父亲相当风光,不仅是应山县中学尖子班的班主任、语文教研组组长,还是颇有声名的青年作家,每个月的稿费都远超工资。
但不幸的是,我1957年出生后,父亲学校的语文教研组全部沦陷为右派分子,父亲更是划为极右被判刑四年,送劳改农场监督改造。父亲前往赵李桥的前一天,是我一岁的生日,他到看守处请假,买了两斤苹果回来看我。听母亲说,我用小手拉着爸爸的手指头,似乎知道他一走就会数年不归,以“抓周”的形式演绎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父女共情。
父亲走后,卫生院领导轮番劝导母亲,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但都被母亲婉言拒绝,她的心中不仅饱含家庭的温情,也固守了人性的善意。也因此,母亲被下放到90里外的马坪卫生所工作。
马坪卫生所医护人员不多,但都经验丰富,他们24小时值班。马坪周边有一个徐家河水库,有时夜间村民炸鱼受伤,血肉模糊送来急救,母亲他们全员上阵紧急施救,直到处置好伤病人员后他们才能休息,第二天还要接着上班。
夏天天气炎热,长疖子的人多深度感染,疮痈范围大,发烧红肿出脓也是很疼痛的。来母亲外科诊室切排脓液,有时血脓很多,溅到托盘和母亲的手上、身上,母亲擦掉脓血继续为病人处置伤口,上消毒纱条,吸脓,包扎好伤口。那时医疗器具、敷料消毒比较简陋,都是自己做棉签、棉球、纱布条等,用蒸锅蒸煮20分钟,放凉后装入消毒磁缸内备用;医疗器具镊子、钳子、刀具消毒后,放入福尔马林消毒液中浸泡。
由于母亲技术精湛,和蔼可亲,深得马坪父老乡亲们的敬重,大家见面都亲切地称她“徐医生”,小孩子们则亲昵地喊她“徐姨妈”“徐阿姨”。尽管如此,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母亲有时候在黑夜里发愣,那是对父亲的思念和担忧。当然,她也会在煤油灯下,给我们纳鞋底做鞋。至今,我还珍藏着母亲为我做的一双棉鞋、一双布鞋,是她退休后的“作品”。
三年大饥荒时,我年纪小因饥饿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身体虚弱,连苍蝇落在脸上也无力拍打,出现了严重的脱肛。大便后,母亲总是及时地托起直肠送入体内,才未导致充血、水肿和坏死。母亲还请求所长帮忙,批了一些猪油指标,只让我一个人专享,一个多月后才逐渐好转。要知道,那时候能够吃到猪油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1963年春,我染上了百日咳。这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症状为阵发性痉挛性咳嗽,且晚上剧咳,一声紧接着一声,呼吸越来越急促,感觉心肝肺都要咳出胸腔。有时候,泪水、痰液和胃里的食物翻江倒海,从口中喷射而出,随后整个人都虚脱了,不能动弹。吐过以后,咳嗽稍稍缓解,母亲帮我清理满脸满身满床的污渍,更换床单和被子。后来,她用大枕巾围在我的脖子周围,阵咳和痉挛的发生有所减少。那一次,母亲衣不解带躺坐在床边,一连数晚。在母亲殚精竭虑的守护下,我终于战胜了疾病,迎来了康复。不幸的是这年秋天,我又染上了伤寒。这是一种肠道传染性疾病,与成人比儿童症状较轻,有母亲的专业照顾,我没有丝毫的担心受怕。
1965年元月小妹出生了,足月出生的她体重却只有两斤九两,像只小猫。那时的物资贫乏,更没有什么营养品供应。尽管舅舅从100多里外的广水挑来了面条、糯米、酒糟、花生油、鸡蛋、鸡等两大筐生活物资,但虚弱的母亲依然没有奶水喂养。小妹是靠米汤、稀粥喂养大的,三岁才学会走路。
“文革”期间,母亲常驻学习班,小妹太小,只能带在身边,她是学习班里最小的学员。后来,小妹又跟母亲一起下放到新河卫生所,她们相依为命。至今我无法想象,母亲花费了多少心血,才让小妹健康长大。
1972年,我和哥哥一起参加工作到广水水泥制品厂,每年回一次马坪老家。1973年,母亲从新河卫生所调回长岭卫生院,我们就回长岭看她老人家。母亲1976年退休时和小妹一起来到广水,厂领导聘请她在卫生室工作。
1978年,我们家迎来重大转折:一是建了房子有了安身之所,二是哥哥考上大学,三是父亲右派平反,重新回到广水中学做老师。此后,母亲就回家开始退休生活,这段时间是母亲、父亲最开心快乐的日子,前半生委屈,一切释然。在家里,两位老人经常哼唱“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日子”“黄河在咆哮”等,仿佛又回到青春年少的激情岁月,那是他们走出去、看世界的起点(父亲和二叔及同伴经历三年多的步行抵达重庆,毕业于国立九中),也让他们经历了从人生高峰跌落低谷的曲折。
母亲最拿手的菜是红烧肉,每次从菜市场买回五花肉洗干净,切成方正小块,炒炸出油放入瓦罐,加酱油、姜、葱、八角、糖等调料,守在蜂窝炉边,小火慢炖,手里还拿本书,看上几页就翻动一下,约一个半小时后五花肉烧成酱红色,油而不腻,入口即化。那是母亲的味道,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红烧肉,让人回味无穷。
1981年4月,厂里选送一人到国家建材局在北京举办的培训班学习,我以考测第一名获得这次机会。当告诉父母亲这个好消息时,他们高兴地问“几个人呀”,我说“就我一个人”。他们不放心我一个女孩子单独出远门,决定由母亲陪我去。
4月的北京乍暖还寒,我们提前三天到达。早晨6点钟到达北京站时,虽然穿着棉袄,仍感凉风飕飕。我们按图索骥,找到建材部报道后,第一站是天安门广场。刚建起不久的毛主席纪念堂庄严肃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国历史博物馆雄伟壮丽,让人肃然起敬。我们喝了大碗茶,吃了面包就经金水桥进入故宫。宫殿的金碧辉煌、珠宝工艺品的琳琅满目和皇家园林的秀美大气,与我们寻常人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能够一饱眼福也让我们深感幸运。
第二站北海、中南海,是名副其实的皇宫后花园。永安桥、永安寺、白塔、九龙壁等景点,至今还印象深刻。中南海在北海南边,是中海和南海的统称,我们来到丰泽园毛主席的旧居,还有颐年堂,是政治局经常开会的地方。毛主席居室内有一张特大床,床上边都是书籍。主席在这里工作生活近二十年,能够亲临其境,我和母亲都十分欣慰。
颐和园是第三站,我和母亲登上佛香阁就已经很疲乏,她说:“太累了,我不想上去,在这里等你。”我鼓励她,等休息一下恢复体力后,一定能上去的。最终,母亲登上了万寿山的最高处智慧海。三天后,在我们学员全部报到、开课之际,母亲一个人返回广水。
1989年8月,为了参观全面完工的“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我陪母亲带着3岁的女儿去了一趟宜昌。那时候,旅游远没有今天普及,当看到轮船经过层层闸门“爬楼梯”的场面,母亲啧啧称赞。那次,我们还游了三游洞、小三峡等景点,母亲虽然60多岁,精神状况相当不错(附图)。她回忆起烽火岁月的流浪生活说:那时候担心受怕,根本没有心思欣赏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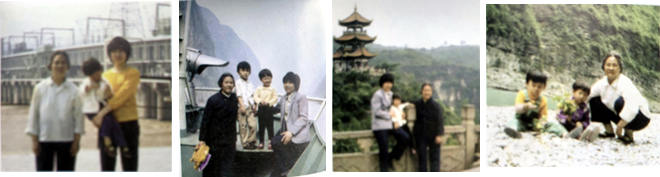
附图:和母亲一起畅游宜昌的留影
但是,好景不长。1992年8月21日下午,女儿跑到财务室告诉我外公生病去医院了。我忙请假心急火燎地向街道诊所奔去,女儿在后面一边哭着一边追,我也顾不了。到达时,父亲已经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了。我就近找了辆板车拖上父亲就又往县二医院奔去。途中,母亲告诉我父亲瞳孔已经散大,没有生命体征了。我悲痛万分仍然坚持要送往二医院抢救,母亲以她的专业素养告诉我,已经没有抢救意义。我才回过神来,将板车掉头回家,准备安排后事。此时,子知(我爱人)已从厂里赶回家,在客厅里放上了门板,我小心翼翼地将父亲抱下板车,走过院子,轻轻的放在门板上。那一刻,我才深刻体会到由于长期肺气肿(因为肺结核吐血,是妻子儿女的牵挂才激励他走出了劳改农场),80多斤的父亲有多么可怜。在子知的安排下,父亲的后事井然有序,哥哥一家、小妹一家也分别从武汉和长岭赶回。
父亲去世后,学校领导及校长、广水教委的领导亲自来看望母亲,询问有什么困难可以帮忙解决。当时母亲精神恍惚,沉浸在失去爱人的悲痛中,子知及时讲起父母一直的心愿,想将小妹调回广水,便于就近照顾。谢谢学校、教委领导,再加上我和子知一直努力配合,小妹夫妻终于在第二年春天顺利调回广水。
1997年9月,母亲时常感觉腹部胀气,食欲不振,大便不畅,便要求我们给她准备一副寿材。其实,子知(我爱人)确实是一个好女婿,早1980年代中就已经为两位老人准备了基料,只是父亲力主火化一直没有动工。对于母亲的要求,他自然尽心尽力。当母亲亲眼看到寿材做好抬回家,才同意10月份跟哥哥到武汉,也有可能她已经预感到什么。到武汉后,母亲于1998年初被确诊为结肠癌,并完成手术和化疗,随后回广水休养。在子知精心的饮食搭配和我的照顾下,母亲身体恢复的很好,我们都以为母亲战胜了令人闻之色变的癌症。没想到,开心的日子只有一年。1999年4月,母亲病情复发,来势汹汹,很快腹部长满包块,已没有再次手术的可能。虽然我们精心照顾,哥哥和嫂子也想尽办法,尽量减轻母亲的痛苦,但她的身体状况直转而下,只能躺在躺椅上,度日如年。受尽病痛折磨的母亲,最终于1999年8月13日上午10点17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母亲这一生,于工作认真负责,救死扶伤,与同事配合默契,沟通顺畅,对患者严谨认真,耐心细致。于家庭,她则像一颗扎根深厚的大树,始终守护家庭的完整与安宁。感恩母亲,她孕育了我们的生命,给了全家最坚定的守护,还是天上最耀眼的星星,向人间播洒善意,并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1480685.html
上一篇:樊群:想念天堂的妈妈
下一篇:星言星语和星月(388):登梧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