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樊群:我的婆婆
||
婆婆离开我们已经25年,再过几天就是她100周年的诞辰。时间过了这么久,如果我再不为她写点什么,那真是辜负了我们多年相亲相爱的婆媳情。
其实,这个题目在我脑海里已经盘旋了很多年。也许,她的故事并不如父母给了我生命那样刻骨铭心,却是多年来我内心里一股源源不断的暖流。至今,第一次见到婆婆的情景依然那么清晰:
那是1983年7月6日,我第一次到先生(男朋友)家上门。他在火车上就跟我讲了妈妈曾经的一些故事,她老人家这辈子吃了很多苦,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大功臣,见到我母亲,你一定要叫她一声“妈妈”,就算我求你了!
看他诚恳的样子,我自然没有理由拒绝。下了火车,穿过一些小街小巷到他们家,敲门后迎接我们的正是婆婆,她微笑着上下打量。
“妈妈!”我的一声称呼,让她非常意外。楞了一下,随后满脸欢喜地对我说:“快进来,快进来!”从此以后,她老人家那历经沧桑的“妈妈笑容”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结婚后,我和先生两地分居。我已经是母校附属医院的内科医生,他却分回老家,在一个镇子上的县二医院理疗室。那时候,我非常羡慕自己的同学、同事,她们大都嫁的是干部或高知家庭,在武汉有现成的婚房,而我只能独自蜗居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幸亏,先生很会“画饼”:10年内,我会让她们羡慕你的!
有一次回广水,妈妈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菜,还带回来新上市的鳝鱼。我起床后看到只有那么几条鳝鱼,居然还死了一条,心里很不高兴,就抱怨了起来。连一斤鳝鱼都舍不得买,先生连忙去问了婆婆,回来告诉我:只剩下那几条,她都买回来了。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不料吃的时候,婆婆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她自己却一块都没有吃。让我真是好难为情。
结婚一年半,我回家生子,是个乍暖还寒的初春。因为儿子脐带绕颈3圈,不得不在先生的医院进行了剖腹产。那时候镇医院没有新生儿室,为了让我休息好,婆婆将刚刚生下来的儿子打了个包,一个人抱回了家。那天晚上,不知道她是怎么过来的,我事后问她,她说喂些温水、糖水就可以了。但对于我,真是不可想象的事。
七天后,我拆线回家了。只听婆婆说过一句话:“把家里的鸡都吃了!”随后是日复一日的喝鸡汤、吃鸡肉(那时候可没有肉鸡)。当地的习俗是月子里不出房门,家人只是每日把她的小孙子抱出去逗逗,晒晒太阳。一直到满月都是很享受的。每次回广水,我都非常放松,享受“自由自在”的时光。这一点,在华农的娘家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父亲非常严厉,回家总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
孩子半岁时,先生考研究生来到了附属医院。有一次,我和先生闹矛盾。我写了封短信放在枕头下面,谁知他悄悄看了却不以为然。我心想:你不在乎我,自然有人在乎。我就把信发了出去。两天后,爸爸妈妈就从广水的家里来到我们的小房子,先生吃了一惊:你们怎么来了?我心里却十分感动。他们二老把先生严肃地教训了一顿,帮我出了一口气。那次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似乎是我们长大和成熟的标志。
婆婆不善言辞,很少话语。1986年国庆节,两家亲家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华农。因为我的父母亲早就听说,在公公划为“极右”劳改的4年里,婆婆没有接受组织上“划清界限”的谈话要求,并从县卫生院调到镇卫生所,守住了先生一家的安宁。他们也听说过,婆婆和公公对我的慈爱,也亲眼见证了二老的豁达宽厚,不卑不亢。离开后,家教严苛的父亲也对婆婆赞美有加,而且发自肺腑。
1991年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办了个“高级英语提高班”,目的是培养中医药英文教学人才。我被侥幸录取,需要学习一整年。那时候,先生刚刚调到肝病研究所,工作十分繁忙。临行之前,我找同事租了对门的一间房(正好同事搬到丈夫的单位住居),接来了公公婆婆,帮忙照顾刚上小学的儿子(之前有阿姨看管,我的父母负担保姆工资)。
一年里,有了公公婆婆的照顾,我完全放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终于,没有辜负组织上的培养,一度成为留学生教学的骨干,出色地完成了多项教学任务,并在1994年晋升副主任医师时获得满票通过,这是后话。
1992年7月,英语学习一结业,我就匆匆忙忙地赶回武汉。到达的第二天,公公婆婆就决意离开,理由是回到广水将家里的院墙整修一番。而我清醒地意识到,二老是为了给我们腾出空间,让我们享受一家三口的恩爱日子。这一次让我深深感受到老人总是全心全意地为后人着想。
那天,是我一个人将他们送到火车站的。当时先生确实比较忙。在武昌站的地下通道,公公上楼梯倾尽全力几步一喘的情景让我百感交集:爸爸妈妈,您这身体需要在武汉才有保障啊!在送上火车那一刻,我的眼泪控制不住的倾泻出来。幸好偶遇到武汉出差的先生过去水泥制品厂的同事,他们看着我伤心的模样,让我放心,一定会带他们安全到家。
一个多月后,一封电报带来了公公离开(可能是心肌梗死)的消息,我们一家三口回到广水,先生悲痛万分,自责不已。此后不久,我们再次回到老家,接婆婆和我们一起生活。每年八九月份接她过来,清明节前后送她回广水家中,小妹妹也随后调回与她一起住居。
时光过得很快,我们婆媳一直感情很好。婆婆在这里除了做饭,空余时间就拆毛线、打毛衣。我们身上穿的毛衣、毛裤、毛背心都是她织的,一代又一代地更新。一针一线,倾注了她毫无保留的挚爱,细密的温情,不仅织进毛衣的缝隙,也织进生活的时时刻刻。
再有时间,她老人家就会坐在沙发上看书,家里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都看了,甚至包括先生他们编写的专业书。老人家看书时,就像一尊雕塑端立在那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地读着,很平静,很关注,没有一点杂念。有一次我问她:您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呀。她说“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可是,婆婆从来没有表现出急躁和焦虑,一切都显得云淡风轻。
有时候,家里会有一些客人,婆婆总是温暖和周到,充满善意。那次,我的妈妈骨折住院,尽管请了阿姨,婆婆也总是做饭、洗衣,毫无怨言。我想,她老人家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肯定也会有一些看不惯的地方,但她从来没有半点表示,是因为她的爱包容了我们,还是确实心满意足,我至今都不明白。
我们住在三楼,阳光充分,婆婆经常为我们晒被子。晚上嗅着太阳的味道入睡,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她照例将被子搭上竹竿伸出晒台后,先生幽默地对她说,您不要每天都享受阳光,也给别人留一点。她大笑起来,自然明白先生担心她太劳累,从此她减少了晒被子的次数。她对自己的生活没有要求,似乎一切都十分满意,我们一家三口每天陪她到学院散步,应该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因为那也是医院和学院的一道风景。
但是,好景不长。1998年秋,万恶癌细胞侵袭了她的升结肠,因为发现的较晚,手术后又由于普外医生缺乏肿瘤外科的精细,而导致肿瘤细胞播散到腹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所疏忽,竟然彩超提示有阴影(彩超医生不认为是肿瘤播散腹腔)而没有警惕,在她的要求下于第二年5月将她送回老家。两个月后,我和先生一起回家看她,却发现腹腔的肿块明显增大,方才吃了一惊,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在婆婆最后的日子里,我们隔三差五回去陪她,每晚轮流睡在她的身边。终于,婆婆的坚韧不屈并未扭转病情的进展,于1999年8月13日踏上了天堂之旅。婆婆走了,留给我们的是25年的自责,是愧欠,是悔恨。不过,婆婆的慈善,为了儿孙的奉献精神,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血液里......

1 婆婆和先生

2 公公婆婆的结婚照(公公的遗墨《沧海拾零》的扉页)

3 婆婆在安顺军医学校(迁往上海后)与同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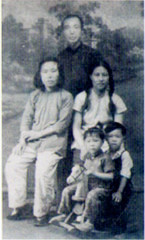
4 婆婆和姑姑带先生兄妹到赵李桥看望劳改的公公

5 儿子满月后的全家福

6 公公婆婆安享晚年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1480343.html
上一篇:张卜天主译“科学史译丛”,已经出版21本
下一篇:医学的觉醒:从神谕到基因的三次跃迁